《吕氏春秋·审分览》知度赏析
【原文】
明君者,非遍见万物也,明于人主之所执也。有术之主者,非一自行之也,知百官之要也。知百官之要,故事②省而国治也。明于人主之所执,故权专而奸止。奸止则说者不来,而情谕③矣;情者不饰,而事实见④矣。此谓之至治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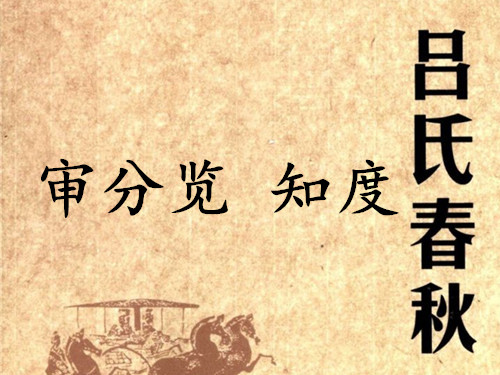
【注释】
①知度:要懂得做国君的方法。此篇阐述的是尹文学派的学说。②故事:这里是两个词,故,所以。事,事情。③谕:使人知道。④见:通“现”,显露。⑤至治:最完美的政治。
【译文】
贤明的君主,不是到处去考察天下万事万物,只要明白国君应该掌握的东西就行了。有办法的国君,不是自己一个人来操办所有的事,只要知道了驾驭百官的要领就可以了。懂得了驾驭百官的要领,因此做起事情来就省力很多,而且国家也就可以达到国泰民安的大治了。
明白了作为一位国君应该掌握的东西,因此权势就可以集中而奸邪就可以制止。奸邪被制止,那么那些游说邪道的人就不会到来,人们的真情就可以明白地表达出来;真情没有被掩饰,事实就可以显现了。这就是说的最完美的政治。
【原文】
至治之世,其民不好空言虚辞,不好淫学流说,贤不肖各反其质。行其情,不雕①其素;蒙厚②纯朴,以事其上。若此则工、拙、愚、智、勇、惧可得以故易③官,易官则各当其任矣。故有职者安其职,不听其议;无职者责其实,以验其辞。此二者审,则无用之言不人于朝矣。君服性命之情,去爱恶之心,用虚无为本,以听有用之言谓之朝。凡朝也者,相与召理义也,相与植④法则也。
上服性命之情,则理义之士至矣,法则之用植矣,枉辟邪挠之人退矣,贪得伪诈之曹⑤远矣。故治天下之要,存乎除奸;除奸之要,存乎治官;治官之要,存乎治道;治道之要,存乎治性命。故子华子曰:“厚而不博,敬守一事,正性是喜。群众不周,而务成一能。尽能既成,四夷乃平。唯彼天符⑥,不周而周。此神农之所以长,而尧、舜之所以章⑦也。”
【注释】
①雕:雕饰。②蒙厚:敦厚。蒙,通“庞”,厚。③易:调换,调整。④植:立,制定。⑤曹:众,人们。⑥天符:所谓上天的命符。⑦章:通“彰”显赫。
【译文】
最完美的世道,百姓不喜欢说空话和虚假的言辞,不喜好愚诬的淫学和没有事实根据的传说,贤能的人和庸俗的人各自都恢复其本来面目。行为真诚朴实不雕饰;敦厚淳朴,以此来侍奉君主。因此,巧的、笨的、愚蠢的、聪明的、勇敢的、懦弱的,都表现出来,于是根据法典来调整他们的官职。官职调整好了,使他们的职位与他们的能力相称。
这样,有职务的人安心于他们的工作,君主不听他们越职的议论;对那些没有官职的人,倾听他们的言论,考察他们的功绩,检验他们的言辞是否虚假。审查这两种人,那么,无用的言论就不会进入朝堂。君主顺从生命的天性,抛弃好恶的思想,用虚无作为一切的根本,把听有用的言论作为“朝”。凡是“朝”,都是君臣之间共同招致理义讨论,共同参与修订法则。
君王服从天性情理,那么讲道理礼义的人就到来,法度的作用就会确立,乖僻奸邪的小人就可以摒弃,可以斥退,贪得无厌的伪诈小人就远离了。所以,治理天下的要务是除掉奸邪;除掉奸邪的根本是整治官吏;治理好官吏的根本是研究方法;研究方法的关键是懂得生命的天性。
所以子华子说:“做事情关键是要做得深厚、专一,而不在于广博,兢兢业业地做好一件事,把天性端正当做一种自己享受的快乐。不和周围一般的大众相同,不随波逐流,而是一心一意地成就自己端正天性的能力。尽了最大努力去做的话就可以成功,即使是四方的夷蛮,也可以使他们安定。只有这样,那些合乎生命天性的方法而生存着的人不求与生命的天性相吻合,却能够达到与天性相和谐的地步。这就是神农为什么可以兴旺,尧、舜为什么可以声名显赫的原因。”
【原文】
人主自智而愚人①,自巧而拙人②,若此则愚拙者请矣,巧智者诏③矣,诏多则请者愈多矣,请者愈多,且无不请也。主虽巧智,未无不知也。以未无不知,应无不请,其道固穷。为人主而数穷于其下,将何以君人乎?穷而不知其穷,其患又将反以自多,是之谓重塞之主,无存国矣。
故有道之主,因而不为,责而不诏,去想去意,静虚以待,不伐④之言,不夺之事,督名审实,官使自司,以不知为道,以奈何为实。尧曰:“若何而为及日月之所烛⑤?”舜曰:“若何而服四荒之外?”禹曰:“若何而治青丘、九阳、奇肱之所际?”
【注释】
①愚人:以为别人愚昧。②拙人:以为别人笨拙。③诏:告。④伐:自我夸耀。⑤烛:照耀。
【译文】
当君主的人往往自己认为自己聪明过人而其他人就愚不可及,自己认为自己心灵手巧而别人就笨手笨脚,如果这样的话,愚笨的人来向君主请示的时候,灵巧聪明的君主就召见他们,召见越多请示的人也越多,请示君王的人越来越多的话,就不会有不来请示的人了。君主虽然是灵巧聪明,但也不是什么都知道的。用自己并不是什么都知道的条件来回答下臣没有什么不来请示的问题,君主就一定应付不过来。
当君主的人多次被臣子弄到走投无路的境地,将凭什么当君主呢?被下臣赶到走投无路的地步,但是没有觉察到自己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地步,他的问题还在于反过来自吹自擂,认为自己十分能干,这样就叫做严重壅塞的君主,他们的国家就一定会遭到灭亡的结果。
所以,有治国方法的君主会依据下臣的能力来任用他们,自己不会去做下臣的工作,只是命令下臣去完成任务而不对他们下诏指点,放弃自己对下臣工作的思虑,放弃自己对下臣工作的意见,安静而虚心地等到下臣把工作做完,不用语言对自己进行夸耀,不夺取下臣的事情来自己做,按照名分来检查他们的实际效果,让官吏自己做自己应该做的事情。
君主用不知道下臣的具体工作来作为治国的方法,以“怎么样了”来作为自己的法宝询问下臣。例如尧只是向下臣问:“怎么样做才能统治到日月照耀的范围?”舜只是问下臣:“怎样做才能征服四面八方边界以外的范围?”禹只是问下臣:“怎样做才可以统治到青丘、九阳、奇肱之间的范围?”
【原文】
赵襄子之时,以任登①为中牟②令,上计③,言于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己,请见④之。”襄子见而以为中大夫。相国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为中大夫若此其见也,非晋国之故。”⑤襄子曰:“吾举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举,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终无已也。”遂不复问,而以为中大夫,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
【注释】
①任登:赵国大臣。②中牟:战国赵地,今河南汤阴县西。③上计:地方官每年年终向上级(或君主)汇报一年内治理地方的政事及赋税的收入。④见:通“显”,显扬。⑤故:“故法”的省略。
【译文】
赵襄子的时候,用任登作为中牟令,任登在向上汇报政事的时候对赵襄子说:“中牟有两位士人叫瞻、胥己,我请你使他们显耀。”赵襄子接见了他们并任命他们为中大夫。相国说:“我猜想你只是耳朵里听说过这两个人,眼睛恐怕是没有真正看到过他们的才能吧?如此轻率地显扬他们为中大夫,这样做不符合晋国的旧法典吧。”
赵襄子说:“我任用任登,是已经用耳朵听过他的为人,用眼睛看过他的做法。任登推荐的人,又要我亲耳亲眼去听、去看,那么我的耳听目视就会没完没了。”于是赵襄子就不再理会相国的话,其他人都就不再问原因,赵襄子仍然任用瞻、胥己为中大夫。赵襄子依据任登对瞻、胥己的介绍来取用人,那么,被推荐的贤人就可以为自己尽心尽力地工作了。
【原文】
人主之患,必在任人而不能用之,用之而与不知者议之也。绝江者托于船,致远者托于骥,霸王者托于贤。伊尹①、吕尚②、管夷吾③、百里奚④,此霸王者之船骥也。释父兄与子弟,非疏之也;任庖人、钓者、与仇人、仆虏,非阿之也;持社稷立功名之道,不得不然也。犹大匠之为宫室也,量小大而知材木矣,訾功丈而知人数矣⑤。故小臣⑥、吕尚听,而天下知殷、周之王也;管夷吾、百里奚听,而天下知齐、秦之霸也;岂特船骥之绝江致远哉?
【注释】
①伊尹:汤商的大臣,为厨师。②吕尚:太公望,周初辅助周王打天下。又名姜尚,因曾钓于渭水故称。③管夷吾:就是管仲,曾射齐桓公。④百里奚:春秋时候秦穆公的贤相,为仆虏。⑤訾:量度。功:数量。丈:长度。⑥小臣:伊尹的氏。
【译文】
君主受到的祸患,一定是在于任命了别人去为自己做事但却不能使用他们,使用了他们之后却又和不明智的人来议论他们。渡江的人依靠的是船,走远路的人依靠的是好马,霸王依靠的是贤能的人。伊尹、吕尚、管夷吾、百里奚,这些人就都是霸王的船和车马。君王如果不用自己的父子兄弟,并不是有意疏远他们;君王任用厨师、钓鱼者和仇人、仆虏,并不是有意抬举他们。
治理国家建立功业的方法,不得不这样。这就好像大工匠建造宫室,度量一下就知道用了多少木料,量度版筑的数量和长度,就知道要用多少人工。因此,任用伊尹、吕尚,天下人就知道殷、周可以在天下称王了。任用管夷吾、百里奚,天下人就知道齐桓公、秦穆公可以在天下称霸了。这难道只是乘船渡江、骑马致远的功力能够相比的吗?
【原文】
夫成王霸者固有人,亡国者亦有人。桀用干辛①,纣用恶来,宋用唐鞅②,齐用苏秦③,而天下知其亡。非其人而欲有功,譬之若夏至之日而欲夜之长也,射鱼指天而欲发之当也,舜、禹犹若困,而况俗主乎?
【注释】
①干辛:桀的邪臣。②唐鞅:宋康王的臣。③苏秦:战国时候东周洛阳人,纵横家,为齐国的相。
【译文】
成为大王成为霸主的固然大有人在,亡国的也确有其人。桀任用了干辛,纣任用了恶来,宋国任用了唐鞅,齐国任用了苏秦,天下就知道他们要灭亡。任用的人不恰当,要想建立功业,这样就好像想把夏至的黑夜延长一样不可能,好像对着天空想要射中水中的游鱼一样不可能,这种事情即使是舜、禹都尚且无可奈何,更何况那些俗陋不堪的君主呢?
-
上一篇: 《吕氏春秋·审分览》任数赏析
-
下一篇: 《吕氏春秋·审分览》不二赏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