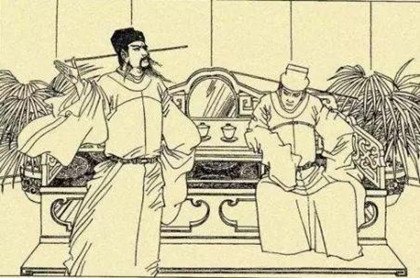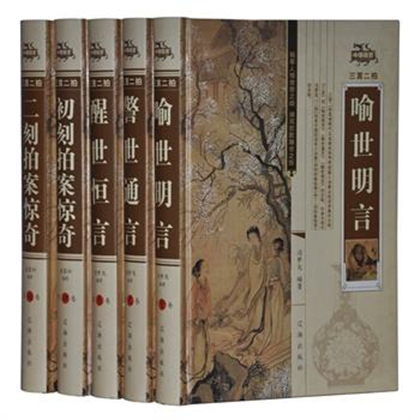汤显祖为什么被称为东方的莎士比亚
400余年前的晚明时期,照旧是一年一度春风徐来,暖意渐浓。封闭在深闺中的杜丽娘,年方十六,但却对屋外的世界一无所知、一无所见。因无心刺绣读书,便步入后花园中寻芳赏花。
不曾料想这是一次致命的游园,原本娇羞的少女在骀荡和暖的春色里,被繁缛的成规习俗压抑、囚禁的自然生命力找到了一个缺口,霍然间喷薄而出,汤显祖以华美绮丽的辞句将心爱的女主人公百感交集的心声袒露无遗。杜丽娘在繁花似锦的自然美景中看到了自己,认出了自己,有狂喜、亢奋,也有“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的伤感、惆怅与无奈。

在脍炙人口的戏曲《牡丹亭》中,汤显祖的笔墨没有止步于展现杜丽娘的伤春情怀,他详细叙写了此后她在梦中与书生柳梦梅邂逅,两情相悦,梦醒之后倍感凄清孤独。她思恋着心爱的梦中情人,缱绻情深,一发而不可收,“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
不多久,杜丽娘在无望的思恋中郁郁成疾,撒手人寰。但神奇的是这并不意味着终结,她的一往情深竟然打动了阎王,最终得以复活,与有情人终成眷属。
汤显祖在剧中着意渲染的便是那磅礴于天地间的至情,“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生而不可与死,死而不可复生者,皆非情之至也。”这一源自天性的至情境界日后在《红楼梦》中发扬光大,衍化出宝黛感天动地的爱情传奇。
在《牡丹亭》问世前的三四年,在万里之遥的英格兰,在伦敦戏剧圈中崭露头角的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也书写了一段感人至深的爱情悲剧。命运之神似乎玩了一场恶作剧,在蒙太古和凯普莱特这两个结有累世冤仇的大族中挑出了一对男女。
血族间的敌意并没有在他俩之间构筑起无法逾越的大墙,强大的阻力反而催生、强化了他们的感情,他们是独自的个人,而不是家庭机器上的一个无足轻重的部件。
在罗密欧眼里,他心爱的“朱丽叶就是太阳”,而在月光掩映的阳台上,朱丽叶吐露出自己的心声,“罗密欧啊,罗密欧!为什么你偏偏是罗密欧呢?否认你的父亲,抛弃你的姓名吧”。
但天地不仁,阴差阳错,两人双双殉情而死。痛惜,哀恸,懊悔,最终消泯了仇恨,换来了两个家族的和解,恰好印证了古罗马诗人奥维德的诗句,“爱战胜一切”。

汤显祖和莎士比亚两人,生活在同一时期,但相隔万里,无缘相识,却灵犀相通。一个生活在晚明时期,中国古典文明早已过了创造力的巅峰,沐浴在烂熟的文明夕阳般绵软的余晖中;另一个则处于在英格兰国势上升时期,百废待兴。他们俩的经历、社会地位、学养各各不一,但都敏锐地嗅吸到了新时代隐隐飘拂而来的气息。
天理、上帝等昔日散发着神圣光彩的词语黯然失色,彼岸世界的允诺和内圣外王的楷模变得遥不可及,他们俩不约而同将目光投向身边生机盎然的感性世界,人的自然生命便是其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被严苛的戒律、习俗锁闭在箱笼中的男女之爱瞬间被激活了,它已不单单是人类繁衍后代的媒介,在他们俩的笔下,本身便被赋予了至高无上的价值。
莎士比亚在《仲夏夜之梦》《皆大欢喜》等喜剧中为爱情唱出了绝美的歌声,而汤显祖在《南柯记》中也以浓彩重墨渲染了淳于棼的痴情,在重逢早已杳然升天的瑶芳公主时,他仍一往情深,执意要她下凡重做夫妻。
他们俩经历了人世的种种变故,笔力变得深邃凝重。通过描绘为复仇犹疑延宕再三的哈姆莱特、刚愎高傲的李尔王、嫉妒成性的奥赛罗,莎翁展示了人性内部的错综复杂与幽暗之处。
在晚期作品《暴风雨》中,阅尽沧桑的普洛斯彼罗像篡位的麦克白一样,发出了人生如梦的感慨:“如同这虚无缥缈的幻景一样,入云的楼阁、瑰伟的宫殿、庄严的殿堂,甚至地球自身,以及地球上所有的一切,都将同样消散,就像这一场幻景,连一点烟云的影子都不曾留下。构成我们的料子也就是那梦幻的料子;我们短暂的一生,前后都环绕在酣睡之中。”
无独有偶,淳于棼在梦境中进入蚂蚁王国,享尽荣华富贵,权倾一时,无奈爱妻离世,最终失宠于国王而被贬遣。更令人诧异的是,这一切全是一场短暂的梦幻。他最后发出感喟,“人间君臣眷属,蝼蚁何殊?一切苦乐兴衰,南柯无二,等为梦境。”

他们俩的肉体生命囚闭在16世纪下半叶和17世纪初期,无法穿越到其他时空区域中。
然而,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瞻望未来,超越各自局促狭促的现实,飞升到一个美丽的新世界,以酣畅灵动的笔墨将人类的种种痛苦、激情与梦想,他们的高贵与卑下,他们的智慧与痴狂一一展示无遗。
他们俩虽与我们相隔四个世纪,但其宏文巨篇依旧弥足常新,不断地激起人们的共鸣与钦佩,仿佛他们的英灵依旧萦回在我们周围,在触发“萧条异代不同时”伤感的同时,一同纠结于“生存还是毁灭”的困惑,体悟生命的大欢喜与大悲哀。
-
上一篇: 汤显祖的后世纪念
-
下一篇: 汤显祖元宵释囚观灯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