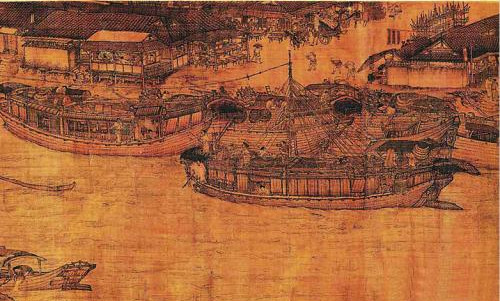行省制的历史作用
洪绂说,元行省是“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省区即军区”,“皆为军事控制区域,各拥相当军需资源;藉以供养驻军,镇压地方,其目的乃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钱穆说,元行省是“一个极不合理的制度”,“行中书省就是一个行动的中央政府,宰相府的派出所。分驻在这个地方来管事。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显而易见,前人对元行省制多有微词和针砭。
需要指出,洪绂把元行省制视为“中古殖民地制度之遗物”的看法是荒谬的。元行省只是蒙古贵族进入中原后所建立的地方军政制度,属于多民族统一国家内部的产物,与入侵外国的殖民活动无涉。况且,元代蒙古本土也设置了岭北行省。倘若按照洪绂的说法,蒙古本土岂不也成了成吉思汗子孙的“殖民地”了吗?

毋庸讳言,元朝统治者设置行省的初衷和直接目的,确实是“以武力维持专制统治与剥削”。确实是“为了军事控制”。但是谁曾料到,元统治者出于军事控制目的而创设的行省,却引出绵延至明清及近代的中央集权新模式。所以,我们对元行省制历史作用的评价,就不应拘泥或局限于“军事控制”、“军事镇压”的初衷,而应从更大的时空范围去探索分析其历史根源和复杂背景。
我们认为,评价元行省制的历史作用,必须着眼于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过程。从形式上看,行省制及其带来的中央集权模式来自蒙元统治者对帝国疆域军事控制的偶然行为,实际上其背后又隐藏着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发展历程的必然抉择。
迄两宋,古代中央与地方的权力结构,主要采用地方分权和郡县制中央集权两种模式。这两种模式“以一个否定另一个”,螺旋式发展。如果说夏商西周所建立的王(天子)为天下共主与诸侯藩屏四方,是一个松散的封建大一统,那么,春秋战国诸侯争霸及兼并就是对夏商西周体制的否定。秦统一后,实行极端中央集权,以郡县统制各地,嬴姓皇族无尺寸之封,“一尊京师而威服天下”,又是对春秋战国诸侯纷争的否定。此前后联系的三形态,恰形成第一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两汉郡国并行,对秦极端中央集权既有继承,又有变通。但魏晋南北朝以豪族大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方镇都督分权或区域性割据,又是对秦汉郡县制中央集权的否定。隋和唐前期,重建中央集权的州县、府兵、科举等体制,又是对魏晋南北朝地方分权割据的否定。自秦汉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构成第二个“正一反一合”阶段。
唐后期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是郡县制地方权力结构的某些部分不甚完善造成的。安史之乱后,藩镇节度使军事、财政、行政、监察诸权在握,可以自募军士,可以占有“送使”等赋税,也可以节制“支郡”,自辟官吏。河朔等镇还能自行拥立主帅。藩镇割据或半割据所造成的内轻外重,显然是对隋及唐前期中央集权体制的否定。两宋一反唐后期藩镇割据之道而行之,立足于收权,而且颇为彻底。
既“收其精兵”、‘制其钱谷”、削其支郡、“稍夺其权”,又以路转运、提刑、常平、安抚四监司为工具收夺州县诸权和监察地方官吏。元及明清统治者承袭两宋制度,继续实行收夺州县官府事权和尽可能集中各项权力于中央的政策,只是在中央集权过程中运用了行省的特殊工具,创立了以行省为枢纽的中央集权,故应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割据的继续与发展。于是,自隋朝始前后联系的三形态及递次否定,又形成了第三个“正一反一合”的阶段。
诚然,就中国的历史环境、具体条件而言,中央集权比地方分权的合理性与进步性明显多一些。隋唐以降,中央集权逐渐取代地方分权割据,也表明了这种优胜劣汰的历史选择。但极端的中央集权很大程度上又是以中央对地方政府“无所分画”和“无所寄任”为基础,是与皇帝专制制度相适应的历史产物,主要是为家天下的王朝大一统服务的。
从这种特定性质、目标及消极后果来看,两宋式的极端中央集权并不是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最佳模式。最理想的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应该是,既能保证中央政府有足够的力量统治好全国,又能保障地方有适度的权力建设好地方。从中国的国情出发,以中央集权为主体,适当添入地方分权的若干内容,应是比较合理和有益的。
关于这个问题,明末顾炎武、王夫之及南宋叶适曾作过有益的探索和论述。顾炎武认为:“知封建之所以变而为郡县,则知郡县之敝而将复变。然则将复变而为封建乎?曰:不能。有圣人起,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而天下治矣……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
顾炎武以进化论的观点看待封建制地方分权与郡县制中央集权的递次兴替变更,还揭示封建制地方分权的缺陷和过失是“其专在下”,多数权益为地方封君占据;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缺陷和过失又是“其专在上”,多数权益为朝廷所垄断。这是独具慧眼的。他还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是达到天下大治的良策。即在郡县制中央集权的现有体制内,部分地吸收封建制地方分权的因素。这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意思。王夫之也说:“封建之天下分而简,简可治之以密;郡县之天下合而繁,繁必御之以简。”显然也是强调郡县制中央集权应在统治方法上与封建制地方分权取长补短,“简”“密”相辅。
南宋叶适亦主张,在郡县制体系内应参酌古制,实行“以一郡行其一郡,以一县行其一县,赏罚自用,予夺自专”的“伯政”。此处的“伯政”,乃殷商之类的方伯之政。叶适的意图也是要重新赋予郡县官吏一些类似于诸侯方伯的治事权。顾炎武、王夫之、叶适三位有影响的政论家,对上述问题的见解大同小异,不谋而合,表明两宋式极端中央集权的弊病已相当突出,亟待改进和变通,创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主辅结合的新模式。
元行省制就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这类新模式。揭傒斯说:“镇以磐石宗,重以分省寄”,《元史·明宗纪》也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做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从法理上说,中央政府以命令授权形式将部分权力交与行省行使,一切治权皆属中央政府,行省只是中央的代理而已。
无论行政、财政、军事、司法诸事权,朝廷总是在直接掌握某些基本权力(如主要军队、官吏任用等)的同时,把相当一部分权力分寄于行省,然后借行省集权于中央。显而易见,元行省制中央集权是秦汉以来郡县制中央集权模式的较高级演化形态,也是两宋否定唐后期藩镇分权的继续,相当于自隋朝始第三个“正一反一合”阶段的“合”。元行省制所体现的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主辅结合,明显优于单纯的中央集权或单纯的地方分权。
特别引人注意的是,在古代中央与地方权力结构的螺旋式发展三阶段中,地方高层督政区的相应演进是至关重要的。元行省又是这类高层督政区较成熟、较完善的形态之一。这类高层督政区往往具有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力,以达到督责郡县,使之完全听命于中央的目标。
然而,西汉州刺史和唐前期十道巡察使或按察使,因其临时和单纯的监察职司而成效有限。东汉魏晋的州牧都督和唐后期的方镇节度使则因监察、军事、财赋三大权集于一身而转化为地方割据势力。两宋转运、常平、提刑、安抚四监司并存的体制,又导致极端的中央集权和地方无权。元帝国建立前后,随着黄河、长江流域的开发及其向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辐射,可供中央政府直接而深入治理的区域越来越扩大。
元行省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应运而生的。元行省本身既是大军区,又是财赋征集区。另外,辽阳、陕西、甘肃、四川、云南五行省又与五道肃政廉访司的监察区完全重合,其它五省内廉访司监察区又分别与行省直辖区、宣慰司辖区相对应。就是说,行省区划多半构成了相应的监察区。
与前述军区、财赋区略有区别的是,军区和财赋区的两大权力统一由行省实施,而监察区的监察权则由廉访司及行御史台独立行使。总之,元行省及其内部特有机制的问世,使军事、财赋、监察三位一体的行省高层督政区成为比较稳定、成熟的建置,而且长期发挥了主要为中央集权服务的作用。明清的三司督抚就是在元行省高层督政区的基础上进一步演化而成的。
然而,元行省制中央集权也发生了一些负面效应。如行省将路府州县各项权力削夺大半,使其处理庶务的正常功能显著降低;行省区划面积过大,对区域经济文化的发展弊多利少等。这些也是不容忽视的。
-
上一篇: 元朝实行行省制的目的是什么
-
下一篇: 行省权力大而不专是什么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