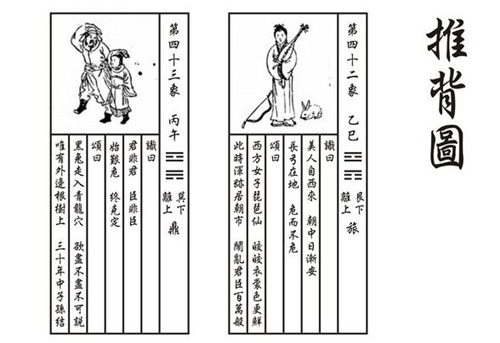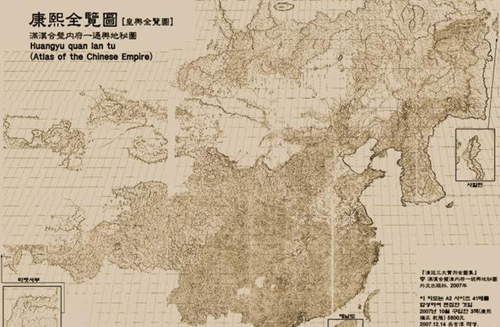《龙藏寺碑》书法赏析
《龙藏寺碑》在典籍中多简作《龙藏寺》,隋开皇六年(公元五八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刻,正书,碑高二点一米,宽零点九米;碑文分别刻于石的阳,阴,左侧三面,阳三十行,行五十字;阴五列,列三十字;左侧三列,上列八行,中列六行,下列二行,右侧无字,碑额楷书“恒州刺史鄂国公为国劝造龙藏寺碑”十五字,结合碑文研读,得知此碑是为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伶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后所立的,原石今在河北省正定县龙兴寺(原龙藏寺)内。

《龙藏寺碑》有隋碑第一的美誉,虽碑未署书者姓名,但楷法精美,气象和穆,出自名人之手当是无疑的,故历来被书家们所青睐,前人大部分谈论《龙藏寺碑》承前启后的意义,存六朝之遗韵,开唐楷之先声。
《龙藏寺碑》首先见著录于欧阳询的《六一题跋》,尔后有阮元,包世臣,杨守敬,康有为等诸学者,书法家作了品评。
六一居士认为此碑“字法遒劲,有欧,虞之体”;阮元断为“直是欧,褚师法所由来”(见《南北书派论》);包世臣更以“《张孟龙》足继大令,《龙藏寺》足继右军,皆于平正通达之中,迷离变化不可思议”(见《艺舟双楫》)的评价极力推崇,并定其为智永所书。
然而杨守敬以为智永名贵谨严,此则瘦劲宽博,故自不同;康有为对此碑评价最高,一个“隋碑第一”(见《广艺舟双辑》)的佳誉把它推到了隋朝书坛的泰斗地位。《龙藏寺碑》在他的《广艺舟双楫·碑品第十七》中列入“精品上”第五位,《张猛龙碑》第一。“《龙藏寺碑》秀韵芳情,馨溢时,然所得自齐碑出者,齐碑中《灵塔铭》《百人造像》,皆于瘦硬中有清腴气.《龙藏寺》变化,加以活笔,遂觉青出于蓝耳。”(见《广艺舟双楫·馀论第十九》)论述了它的师承,取法于齐碑。
除此之外,评价《龙藏寺碑》的还有很多,现拈出数则:黄云认为观此碑,“知欧虞褚薛公衣钵相承”;莫友芝认为此碑与唐“王居砖塔铭皆一家眷属。前辈至谓砖塔乃集此碑字为之,固不必然,亦可见波澜莫二矣”。
可见这些实言不虚的中肯评价是来自内心的体悟。再如张宗祥的“其拙处如小儿学书,,其劲处虽善书者不能及”(见《书学源流论》)。故知《龙藏寺碑》在整个书法史上的地位是不可忽视的,就连大名鼎鼎的唐大书法家柳公权所书的《神策军碑》也没有这份殊荣。
在欣赏和研习《龙藏寺碑》时,要达到更好地撑握此碑书风应注意以下三点:
一、方圆兼施,藏露合一,动静结合的用笔.《龙藏寺碑》出现在南北文化融汇的隋朝.在起笔上,已不再像《始平公造像》等诸北碑那样一味方正,也没有《崔敬邕墓志》一味的圆笔,而是把方圆更好地结合在一起,形成藏露合一的线条,使笔画显得挺拔劲秀;粗细变化恰到好处,为初唐诸家书风的形成铺开了先路.碑中时而出现行书的笔意,使《龙藏寺碑》的楷书静中寓动。
二、疏朗端雅,方正宽博的结体给《龙藏寺碑》的书风增添了几分魅力.它变北碑的欹侧为端庄,变右肩耸,左脚展的北派结体为基本保持均衡平直,左脚收敛,右肩自然放置有别于前代的形体.碑中字形较扁,长横平稳,有些字还出现隶书的雁尾如“方”。
我国汉字的形体变迁到汉代的隶书,可能说是"赴便捷"了,由汉代到魏晋南北朝,是逐渐向楷书的过渡阶段,至隋代才基本完成,这样汉字形体就基本固定.这里所谈的《龙藏寺碑》就是一方不朽的代表作,中正宽博,和穆凝重,保存了六朝碑刻的气度.褚遂良《孟法师碑》敬客《王居士砖塔铭》甚至张旭《郎官石记》,都承延了《龙藏寺碑》的香火,它们在结体上几出一辙。
三、“寄灵秀于质朴,寓蕴藉于淡雅”(王壮弘语)的风度。以北碑书风为基调,融入南方遒润的《龙藏寺碑》,在书法发展史上别具一格,质朴之中有灵秀,蕴籍而俊逸,貌若温和宁静,行笔刚劲放纵,翩翩有致.继承了魏晋书法的洒脱俊逸,又存了北碑的质朴,可以说是既吸收前人之精髓,又开导了唐风的先河。
谈到这里,不妨略窥一下隋人的文化思想:在六朝时代,被后人康有为喻为“无所不备”的北碑诸造像,都是一般庶民崇佛思想的见证;而处于同时期的南方,则游学于大自然,谈“玄”论道,使其书法形成独特的晋韵.隋朝统一南北后,封建帝王为了维护阶级的统治,重振了长期处于没落的儒家思想,“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在这种创作思想影响下的短短三十八年中,就开创了一代文质彬彬的新书风。
“融南北之精华,以达到中和的境界”(沈浩《隋代楷书论》),《龙藏寺碑》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诞生的。端庄且灵秀,凝重而不板滞;宽博又紧约,疏朗而不显松散,“荟萃六朝之美”(见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取隋第十一》)所以它在整个书法演变史中有"上接两晋笼罩三唐"(见杨守敬《学书迩言》)的特殊地位。
《龙藏寺碑》在历来书家评论中,虽然各家所持的看法略有不同,“承上启下”的作用是无二致的。但《龙藏寺碑》并不仅仅是“承上启下”,则是它对当今书法创作有着更重要的意义:即它为我们作出了“碑贴结合”的表率。《龙藏寺碑》的诞生是有着它一定时代背景的,在隋之前的北朝工匠书法,已经把雄健恣肆的风格发展到极至,无论隋人无何在这方面努力也是无法逾越的;而在南方的尚韵书风里,文化思想决定隋人更不能跳出二王的桎梏。
在这种困惑下,隋人选择是聪明的,他们“既没有沉浸在北方粗犷的书风里,又没有陶醉在南方秀媚的王国里”(见《书法学》,陈振濂主编)而是选择了“碑贴结合”的新道路,形成了中和美的隋代书法。
鉴照今日的书法创作,确实有几分“隋人的困惑”,碑在清季兴起,到民国则已创盛,走碑派也许只步前人后尘;经典的贴学,今人创作的行草风格往往又离觉斯,青藤,舟山等明清诸大家不远.在这种迷惘下,为什么不可另辟他途?痛快来一次重演“隋代书法”的绝技-碑贴结合,定能会给当今书法创作带来新的生息!
当然,这不能只局限于外在形式的结合,更要挖掘它们内在的潜力,使其有机的融合。在这方面,《龙藏寺碑》给我们提供的经验是无穷的.希望造诣较深的书家为我们辟开先路,使这种风格能早日形成与成熟。